当法律和天理发生冲突,古代中国如何判决?

几乎每一起涉及弱势群体“复仇”的热点事件,都能让舆情和法制之间的关系,骤然紧张起来。当年的杨佳、张扣扣,最近内蒙、东北等地的几起案件,无不如此。
在“法治”成为核心价值观的今天,底层民众竟然铤而走险,选择暴力复仇,不少人将其解读为,这是求告无门后的无奈之举,若按现有法律制度惩处,是不符合天理的,从而引出法律和“正义”之争。
略巧的是,前段时间,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老师出版了一本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,书里有大量类似冲突的古代案件。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法特别注重“天理”和“人情”,所以,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很多热点事件,以及司法实践,可以说极具启发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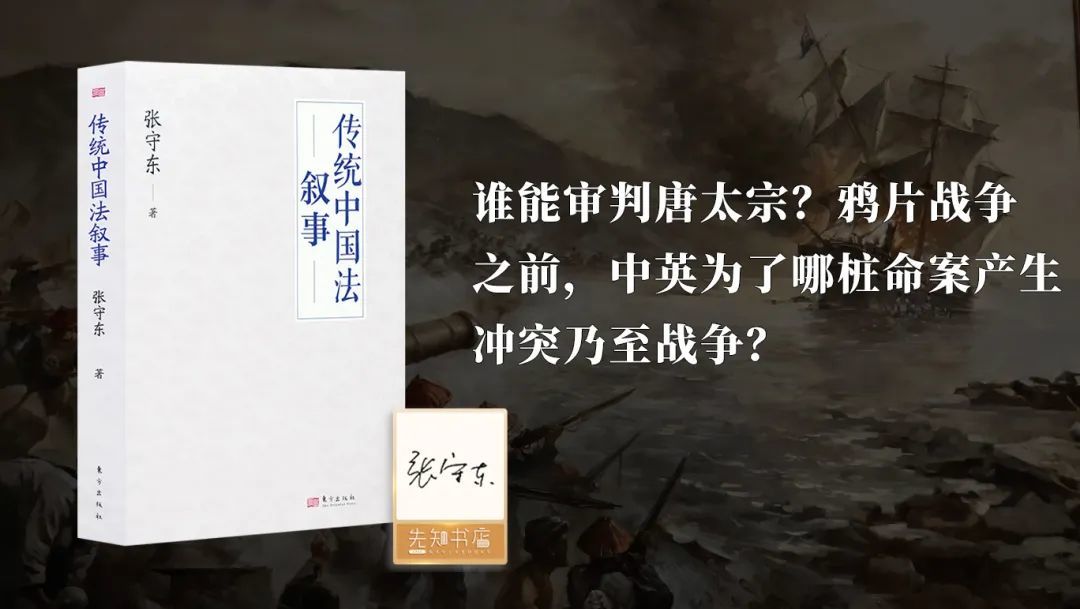
张守东老师这个名字,熟悉人文社科、知道哈耶克的读者是有印象的——是的,他就是哈耶克名著《法律、立法和自由》的译者之一。所以,看到“传统中国法叙事”这个名字,估计不少朋友会有“走错片场”的感觉。
但其实这不奇怪,而且能写好“传统中国法”这个话题,还非如此不可——因为在今天这个独特的时代,写好传统中国法的前提,先要具备从世界看中国的高度和认知储备,才能准确把握传统中国法的独特价值,进而古为今用。张守东老师刚好是那个对西方法律思想、政治哲学有多年研究和独到理解的人。
即便如此,一看到“传统中国法”这几个字,还是会劝退很多人,从而错过这样一本好书。究其原因,来自于以下三个误解。
误解1:传统中国法简单粗暴,而且欺软怕硬
受一些畅销书或影视剧误导,很多人对传统中国法的认知,要么是法家主导下的严刑峻法,要么是放任侠客“快意恩仇”的无所作为。
按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的阐释,严刑峻法只在秦朝作为主体施行,汉朝以后,儒家的仁政、德治为法律塑造了新的范式,“德主刑辅”成为主流,对天理、人情的兼顾,使很多判例充满了人情味。
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案例:武则天期间,徐元庆改名换姓到一家驿站作仆役,只为有朝一日,能等到当年的杀父仇人。最终天遂人愿,大仇得报,然后自首。
案子惊动了朝廷,众大臣吵得昏天黑地。最终,武则天纳取陈子昂的提议:处死,并立碑表彰,依据是“在礼,父仇不同天;在法,杀人必死”。然而,即使给予了如此多考量的判决,还是被柳宗元痛批:如果父亲是被枉杀,徐元庆求告无门,复仇就是替天行道,理应表彰并释放,这个判决,天理不彰。

“当法律与天理产生冲突时,以天理为准。”这是传统中国法的基调。
透过《传统中国法》一书不难发现,法律与天理之间的最佳关系是:法律是对天理的表达,当两者发生冲突时,首先要反思的是法律是否出了问题。有个专业的说法叫“恶法非法”,而判断法律是善还是恶的主要依据,就是法律是对天理的捍卫还是违背。
至于“快意恩仇”,只要具备基本的逻辑就知道并不可能。古代中国法自成体系,虽然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只是一句口号,但朝廷可不“惯着”那些江湖儿女。影视剧里那些好汉随意夜潜别人家“劫富济贫”,是冒着生命危险的——唐朝便有这样一条法律:夜无故入人家,主人将其杀死无罪。这条规定一直持续到清朝。
误解2:传统中国法是与世界文明对立的另类
不少人被个别西方学者片面的批评所误导,认为古代中国缺乏民法,或者把法律制度简化为皇权专制的附庸,从而把传统中国法当成完全与世界文明对立的另类,不足一观。
打开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就知道,古代中国确实没有“民法”之名,但各种杂法、律令、乡规、俗例,其实都是民法,不仅清晰,而且凝练。1920年全国搞过一次大调查,发现从古代沿袭下来的,一共有三千多则民法习惯,陈陈相因,“民法”从来不曾在中国缺席过。
至于“法律是专制的附庸”,亦是误解。秦制两千年,大一统加皇权专制,百姓的自由和权利不值一提,这是事实。但是,这不等于没有法制,没有程序。事实是,官员审案时并不敢为所欲为,因为案卷不仅要层层复核,上级部门还可能随时抽查。王朝还为民众设计了一整套信访、申诉程序,一旦出现冤假错案,官员仕途就会大受影响。

我们都听说过“三堂会审”。三堂协同办案从唐朝就开始了,不同时期各有司功能略有调整,但整体运作基本一致,以明清时期为例:刑部负责普通百姓的审判,都察院负责官员的审判,为防止徇私舞弊,两衙门的审判结果需交大理寺复核,此之谓二审。大理寺如果不认可,再交皇帝“圣裁”。
 而同时,都察院还会监督刑部和大理寺在一审和二审的过程中,有无违法行为。一个部门初审,一个部门复核,另一个部门监督,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审案流程。顺便说一句,这个设置,后世多有参考,甚至沿袭。
而同时,都察院还会监督刑部和大理寺在一审和二审的过程中,有无违法行为。一个部门初审,一个部门复核,另一个部门监督,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审案流程。顺便说一句,这个设置,后世多有参考,甚至沿袭。三堂会审,则指为减少一审、二审及监察过程中的耗时,以及体现兼听则明的办案理念,三堂首脑联席审判,尤其,基于案件的敏感和重大,三堂会审甚至无权出具最终判决书,要上报皇帝等候“圣裁”。
三堂会审是为封堵一家独大的司法漏洞、防止发生冤假错案而做的制度保证,确保案件在初审、复审和终审三个阶段得到审慎审理,体现了传统中国法古朴的正义原则。
可见,对“官员枉法”的监督治理,对程序正义的重视,一直以来,都是中华法系的重要部分,传统中国法与古代西方法,只有程度和方法上的不同,并无法理本质上的径庭。
误解3:传统中国法已成古董
有些人想当然觉得,法律只是对现实的解释和应用,是一时一地之事,在已告别帝制一百多年的今天,传统中国法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,对当下已没有实用价值。
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一书,用各种“古今一理”的案例说明,首先,所有的立法都是寻求共识的产物,那么,这种共识,理应含有古人的司法智慧。
事实上,无论古今中外,法律背后都有一个最高原则,违反该原则就不能叫法治。这种最高原则,在西方叫自然法(也有追溯到《旧约》的),在传统中国叫天理,也就是说,法律必须符合天理。所以,传统中国法中的天理,既是普世的,也是永恒的,天理不会过时,而应该在继承中不断阐扬,比如敬畏天地、尊重信仰、仁义礼智信,等等。
在古代,每当发生天理与国法相冲突的案件,上下都会列为头等大事,没人敢掉以轻心,最终也大体能在法律与天理之间找到平衡。这一点,是传统中国法对当下法治最重要的借鉴意义,却也是一直被忽略的地方。

其次,民众的关切点,历来为立法和司法所重点考量,古代法对此进行的三千多年尝试,是一笔丰厚的财富。而法律的本质,其实就是代代相继的经验——法律,根本上来自社会的规则,而社会是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,因此,所有的法律都离不开传统。
基于此,张守东老师认为,对传统中国法的漠视,不仅是对三千年积淀的极大浪费,其对天理和人情的背离,更是对普世法则、社会规则、法律经验的人为切割,极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适,乃至混乱。
远的不说,呼和浩特之后,又发生多起类似案件,不重视此类案件的发生机理包括处置方式,极有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连环效应,摧毁已日益脆弱的社会道德根基。
因此,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出炉之时,就将是再度引爆舆论之刻,而焦点一定而且仍然是:当法律和天理产生冲突时,法官应该怎么判?
可见,无论是为当下棘手的法律问题找参考,还是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,“传统中国法”都是绕不开的“捷径”。
然而,几十年来,各门类图书都呈爆炸式增长,唯独传统中国法领域,长期以来一直古井无波,其丰厚的法学智慧和法理思维,不为今人所知和所用。

张守东老师正是基于对该问题的关切,才写作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一书。以张老师的法学造诣、对中西文明精髓的洞察,以及卓越的文字表达能力,假以时日,本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,应是大概率的事情:
◎法学造诣深厚,是写好任何类型法律读物的前提条件。
近些年来,各种类型的法律读物相继出版,无论是侧重法学理论的王泽鉴先生,还是为社会普法功不可没的罗翔老师等人,他们的法学造诣都是深厚的。在传统中国法领域,深耕多年的张守东教授是一方重镇,本书细致呈现了传统中国法的原貌,让读者得见一个真实的传统法律中国。这得益于他同时还精通史学和国学,通晓古代法背后的时代沿革和风土人情,解读各种案例时,“触角”随时可以抵达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◎贯通中西学理。
无论法理,还是技术层面,传统中国法绝非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。相反,都具有普适性的地方,在技术层面,犹有胜之。如前所述,张守东老师亦深受西方文明洗礼,不仅精通中国法,亦深研美国宪法,还教授中西伦理比较,他还是一名JD徒,这种贯穿中西的视野,使他能基于古今对比和中西参照,把传统中国法里最值得称为遗产的,提炼成这本书。
◎最值得一提的是,本书一改法制史、法理学作品教科书式的写法,以很多充满冲突的法律故事,以及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来展开,比如,谁能审判李世民?王安石、司马光为何为一件杀夫案争得不可开交?为何说鸦片战争的发端,居然是中英在一场民间命案里的法律分歧?这些以法律为内核的故事,也同时帮助我们打开一道窥视中国历史的“旁门”,视角独特,且基于张守东老师的生动文笔和独特的“厚描写”手法,饶有趣味。
法律是一部演化史,少了传统中国法的视角,无论对法治,还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,都是残缺不全的。
